
靠谱卖香烟微信号
解密联系:123456
更新时间:
参加交通安全统筹的机动车发生事故后赔偿责任如何确定
参加交通安全统筹的机动车发生事故后赔偿责任如何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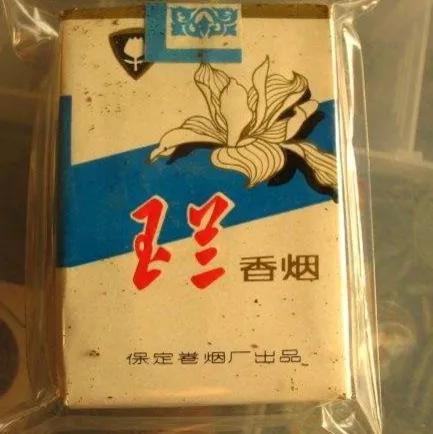
淮南检察
作者:程啸 姜耀飞 宋丽燕
新闻来源:《人民检察》杂志
特邀嘉宾
程 啸(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姜耀飞(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三级高级检察官)
宋丽燕(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基本案情
杜某驾驶非机动车与方某驾驶的挂靠在甲公司名下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杜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杜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方某负事故次要责任。肇事机动车在乙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甲公司还为肇事机动车在丙公司参加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后者责任限额为160万元。在丙公司的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条款中,有如下内容:“服务合同是具有显著行业互助性质的民事射幸合同,不适用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统筹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统筹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统筹人的请求,统筹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被统筹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无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统筹人请求赔偿。”“被统筹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统筹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统筹人不得向被统筹人赔偿。”
杜某近亲属因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将方某、甲公司、乙公司和丙公司诉至A县法院。经查明,杜某在该事故中遭受的损失总额为150万余元,乙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可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7万元,财产损失5000元。除此以外,由于肇事机动车一方在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且杜某驾驶非机动车,肇事机动车一方应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计53万余元。
一审判决认定,方某赔偿杜某近亲属70.5万余元,甲公司对该赔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乙公司对上述款项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17.5万元,丙公司对上述款项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53万余元,上述责任均先于方某和甲公司履行。一审判决生效后,甲公司不服该判决,向B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B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申请。甲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和裁定,向A县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该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是,甲公司因与杜某近亲属就执行问题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检察机关遂终结对该案的审查,并向A县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该类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并在今后办理该类案件过程中准确认定事实、严格适用法律,以促进行业治理。
分歧意见
关于甲公司和丙公司就肇事机动车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签订的服务合同的效力:
第一种意见认为,丙公司经营的“交通安全统筹”实质上属未经批准变相经营保险业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有关合同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丙公司虽然无经营保险业务资质,但是以肇事机动车参加交通安全统筹为内容的服务合同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一般的射幸合同、无名合同,应自其成立时生效。
第三种意见认为,该合同效力应当具体分析确定。若其真实体现了交通运输企业为加强行业互助、提高抗风险能力开展的交通安全统筹业务,可认定为属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范畴,具有法律效力;若其内容系以统筹业务为名行保险业务之实,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产物,应认定其无效。
关于丙公司在该起交通事故中承担何种责任:
第一种意见认为,交通安全统筹实际上相当于普通商业保险,甲公司和丙公司之间建立了真实的商业保险关系,有关服务条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根据民法典第1213条,杜某在该事故中遭受的150万余元损失,应由乙公司赔偿17.5万元,其余132.5万余元损失按照肇事机动车一方承担的责任比例计算后的53万余元应由丙公司先行承担。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公司和丙公司之间仅系一般合同关系,丙公司并非该起交通事故直接当事人。因此,在交强险限额以外的53万余元赔偿应由方某和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者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据有关服务合同另行向丙公司追偿。
第三种意见认为,根据有关合同条款,交通事故发生后经甲公司提出请求,丙公司应直接向第三者赔偿其遭受的损害。因此,若甲公司请求丙公司直接向受害人方赔偿,甲公司、方某和丙公司应共同对上述53万余元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研讨问题
问题一:关于交通安全统筹合同的法律效力
人民检察:
交通安全统筹是运输企业行业内较为常见的一种“互助”形式,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观点认为,从有关合同条款、权责分配来看,交通安全统筹已经成为货车司机或运输企业的商业保险“平替”。如何界定交通安全统筹的法律性质?该案中,甲公司和丙公司就肇事机动车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签订的服务合同效力如何?
程啸:
所谓交通安全统筹是我国机动车交强险制度尚未建立,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商业保险尚不完善时代的产物,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已经确立了交强险,保险法对于商业责任保险也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应当继续承认交通安全统筹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事交通安全统筹的公司实际上从事的是交通事故的商业责任保险经营业务。保险法第6条明确规定:“保险业务由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保险业务。”这就是说,保险业务并非任何民事主体都可以从事的民事活动,而必须是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和相应的保险组织才能经营,从事交通安全统筹的公司不属于可以经营保险业务的法定主体。保险法第15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擅自设立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者非法经营商业保险业务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从目前情况来看,从事诸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等交通安全统筹业务的公司不仅不是保险公司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而且这些公司大部分注册资本很低(实缴资本更少),缺少运营兜底交通安全统筹业务的资金实力,难以有效保障车主和被侵权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法律法规明确禁止非法集资行为。国务院2021年公布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第1款将非法集资界定为“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交通安全统筹并非局限性的、一对一在特定主体之间成立的合同关系,而是以一对多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已经成为变相的非法集资活动。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对于保险业务必须由保险公司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任何违反该规定的单位或个人与他人订立的合同都属无效合同。故此,该案中甲公司和丙公司就肇事机动车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签订的服务合同属无效合同。
姜耀飞:
对合同性质和效力的判断是审查合同纠纷案件的基础和前提。该案中,交通安全统筹合同的法律性质是一种非典型无名合同还是一种保险合同,直接关系案涉合同效力的判定,从而对合同法律效果、赔偿责任承担产生关键性影响。对于合同性质,应结合订立合同的目的、合同内容和具体情况,依据合同主要条款所约定的当事人各方的核心权利义务关系来全面理解和准确认定。交通安全统筹最早系大型运输集团为提升公司内部车辆保障水平而设立,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到,“鼓励运输企业采用交通安全统筹等形式,加强行业互助,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由产生背景观之,交通安全统筹目的在于积累事故理赔专用资金,实行统一调剂和经济互助,帮助企业减少经济赔偿压力,保障事故当事人合法权益。由合同实质观之,交通安全统筹实际上是一种行业互助,并不以营利为特征。因此,如果交通安全统筹合同真实体现了互助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基于政策提倡、政府支持并体现了民事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似无理由对其作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可将其视为一种民事领域的非典型无名合同;如果脱离了互助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征,以营利为目的、由自然人出资成立安全统筹服务公司以统筹业务为名行保险业务之实,则此时的交通安全统筹合同作为商业保险的“平替”,实为保险合同。所以,对案涉交通安全统筹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其真实体现了交通运输企业为加强行业互助、提高抗风险能力开展的交通安全统筹业务,具备互助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可认定为非典型无名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其系以统筹业务为名行保险业务之实,则因违反保险法第6条、第67条第1款等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而无效。
宋丽燕:
交通安全统筹从法律性质上应评价为一般的射幸合同、无名合同,不属于保险合同。首先,从经营主体上看,相较于保险合同,其经营主体并非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也不具备经营相关保险业务的资质,故其所经营的交通安全统筹不属于保险。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民辖24号案件中的裁判观点表明,交通安全统筹虽具有保险合同性质,但因经营主体开展此项业务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仍应按照一般合同纠纷评判。再次,从行业认知来看,近几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及各地分会纷纷发布风险提示函,提醒广大车主,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虽然交通安全统筹合同不属于保险合同,但在当前法律或行政法规并未将交通安全统筹规定为违法性、禁止性行为,甚至还有政策性文件鼓励采用安全统筹、行业互助等形式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的背景下,直接认定交通安全统筹是违法行为,于法无据。该案中,交通安全服务条款明确说明该服务合同是具有显著行业互助性质的民事射幸合同,不适用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在没有其他变相经营保险业务表现(如混淆保险合同与服务合同等)的前提下,因该合同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合法有效。
问题二:如何确定涉交通安全统筹纠纷的管辖法院
人民检察:
有观点认为,因参加交通安全统筹的机动车发生事故产生的赔偿纠纷系侵权责任纠纷,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也有观点认为,该类纠纷主要源自统筹人和被统筹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系一般合同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还有观点认为,该类纠纷应适用保险合同纠纷管辖的有关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该案中的民事纠纷属于什么性质?应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程啸:
首先,因参加交通安全统筹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而产生的赔偿纠纷中,基于交通事故而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可以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是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如违反运输合同)。如果提起的是侵权之诉,即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作为案由,那么侵权责任的成立和承担是此类案件中最核心的问题,而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都是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分散,处于从属性地位,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侵权行为,则不会产生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承担问题。故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应当依据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来确定管辖法院。其次,因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效力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保险合同纠纷,交通安全统筹公司不属于保险公司。该类纠纷主要源自统筹人和被统筹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系一般合同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姜耀飞:
该案存在多重法律关系,一是方某与杜某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二是方某与甲公司之间的车辆挂靠法律关系;三是肇事机动车交强险投保人与保险人乙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四是甲公司与丙公司之间的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法律关系。
据此,可从两个层面确定管辖法院:第一,依据最高法2022年修改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4条关于“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和最高法2020年修改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规定,方某与杜某、甲公司、乙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在杜某近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诉讼中一并解决。基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系侵权之诉的性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第二,杜某近亲属起诉丙公司,其依据的法律关系是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法律关系,与前述侵权法律关系构成两个诉讼标的。根据诉讼法相关原理,一个案件中通常只能有一个诉讼标的。如前所述,方某与杜某、甲公司、乙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在侵权诉讼中一并解决是因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设计。该案中同时审理侵权和交通安全统筹合同两个法律关系并没有法律依据。因此,甲公司与丙公司之间的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基于丙公司并非保险公司,案涉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或为非典型无名合同,或为无效之保险合同,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4条关于一般合同纠纷管辖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宋丽燕:
涉交通安全统筹纠纷类型较多,比如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交通安全统筹合同纠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等。该案中,核心纠纷应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正如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时,也是主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并将侵权人方某、被挂靠单位甲公司、保险公司乙公司和经营交通安全统筹业务的丙公司一并起诉至法院。所以,该案在管辖权确定上,应当按照侵权纠纷的管辖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问题三:交通事故受害方能否直接向机动车统筹人求偿
人民检察:
交通事故受害方能否直接向涉案机动车统筹人求偿,决定了前者能否将后者列为民事诉讼被告,也直接影响有关赔偿义务的现实履行结果。该案中,杜某近亲属能否直接要求丙公司赔偿损失?
程啸:
由于交通安全统筹合同不属于保险合同且为无效合同,故此,交通事故受害人无权直接向机动车统筹人请求赔偿,不能将后者列为民事诉讼被告。只有参加交通安全统筹的公司,在该案中为甲公司,可以要求丙公司承担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对此,根据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姜耀飞:
该案中,方某驾驶挂靠在甲公司名下并在乙公司投保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侵害杜某合法权益。在杜某死亡的情况下,杜某近亲属可以直接要求方某、甲公司、乙公司赔偿损失。合同具有相对性,其仅对缔约方产生效力,除合同当事人外,其他任何人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上的义务。我国现行法律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规定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可由承保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是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无论将案涉交通安全统筹合同认定为非典型无名合同或无效之保险合同,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均不能适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杜某与丙公司既不构成侵权法律关系,亦非合同相对方,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杜某近亲属不能直接要求丙公司赔偿损失。
宋丽燕:
在保护实体权益、保障程序权利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为当事人提供一次性解决纠纷机制。在明确统筹合同有效、保障各方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将交通事故侵权赔偿纠纷与交通安全统筹合同纠纷在同一案件中处理,不仅有利于事实认定的同一性,也能够减少当事人讼累,及时有效保护被侵权人权益。但上述结论在适用法律规定时,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交通安全统筹不属于保险,故不应直接适用保险法或《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其次,可以考虑交通安全统筹合同中的条款设置,具体分析认定。若案涉统筹服务条款约定“第三人有权直接向统筹人请求赔偿”,则成立“真正的利他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22条第2款,被侵权人可直接向统筹人请求赔偿。还可以根据统筹人在诉讼环节的意思表示来确定是否将其列为被告。若丙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愿意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则成立债务加入,根据民法典第552条的规定,杜某近亲属可直接要求丙公司赔偿损失。
文稿统筹:王小飞 (《人民检察》编辑)
- 珠海港:拟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
- 三峰环境集团积极助力重庆夏季电力保供
- 刚刚!港股大跳水,地产全线重挫!牛市旗手,强势拉升!什么情况?
- 中银证券大跌3.77%!华宝基金旗下1只基金持有
- 美股异动|晶科能源(JKS.US)涨逾6% 入围大唐集团光伏组件集采
- 熟悉熟练月线级别的三种形态